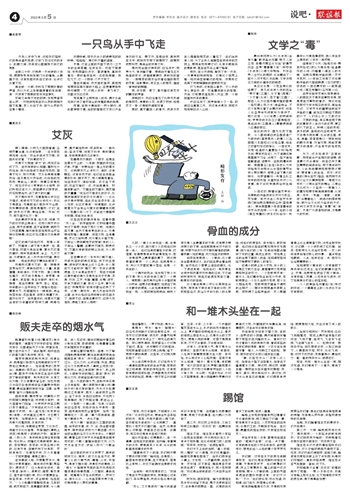踢馆
汪志勇
■汪志勇
“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对手!”这句网络热句,更适合形容年轻时的我。那年,我每天都到公园习武,自我感觉木佬佬好!心也就飘了,一直想找个练家子切磋切磋。当然,也是有贼心没贼胆,梦里自己已经是一流高手,现实中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但比我自信心还爆棚的人,在一天清晨,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叫峰,有着瘦长的外形,要是再来个长须,妥妥的电影里绝世高手的形象。
“隔壁县开了个武馆,我们明天要不要去讨教讨教?”峰说话,总是那么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且不苟言笑,若是边上有别人,你还不能确定他是跟你说话。
“合适吗?明天可是年初二。”我倒不是在乎节日里的讲究,而是担心过年出门,车马费猛涨,吃的价格也是成倍翻。
“放心,又不是很远!”峰大侠言语中似乎有些不屑。他那副永远傲慢的表情,激起了我的情绪,他大概以为我怕了。
第二天,我们挤上中巴车,之后又转乘三轮摩的,“突突突”的一路震到目的地。
馆主不在。馆主老爹看两个年轻人出现在他面前,开口就说找他儿子,有点不知所措,他也许知道习武人的规矩。“来来来,先吃饭。”他满脸堆笑。
我们才不上他的当呢,“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个道理,我们还是懂的。峰面无表情地拒绝了。当我们俩走在小镇上,才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当地只有一家旅馆,还不接客,理由是自家亲戚来住满了。想填饱肚子,那个老板娘说:“我这是给亲戚做的,匀点出来给你们吃。”
吃好饭,回到武馆。峰大侠等馆主老爹开口说留下来住,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条件是我俩要住一屋。这是武侠片看多了的后果,怕被人暗算。
峰晚上发现武馆里有两位操着北方口音的教练,就又提出了切磋一事。教练肯定不会答应,人家按现在的话来说,也是打工的,干嘛陪你玩命。在这里,最重视武馆生存的,只有馆主和他家人。
学生中本地人没有,都是说话翘舌音的。“距离产生美”,这话一点不错。还有就是本地的乡村条件渐好,能吃苦练功、想凭此出人头地的青少年寥寥无几。
我们跟一对来自北方的表兄弟聊得投缘。他们也是在河南听说馆主本领高,于是就来学艺。他们单薄的衣襟,床上又是薄被子,墙上的窗户还没有玻璃,更令人不解的是,上面的气窗连遮挡的塑料布都没有。“你们不冷吗?”“不冷。”他们很乐观,我也无语,我知道,出门在外,吃苦是必修课。
教练被峰磨得没办法,于是就放录像带给我们看,是他们在县体育馆表演的录播,无非是头顶开砖、手指按停旋转的风扇等。
当晚,我们睡着馆主家的厚被子,仍然觉得冷。
第二天一大早,峰就起床练功去了。等我起床,一个年轻点的教练问我:“你们到底来干啥的?我昨晚看见你朋友在楼外面练功。”我笑而不答。
馆主老爹仍然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吃早饭,对儿子啥时候回家避而不答。无奈,我们只能打道回府,在回之前,峰很有风度地去街上买了点东西(钱是我们平摊的),算抵作招待费。馆主老爹客气地推辞一番后,收下礼。
我和峰再次坐着“突突突”的摩的离开了那里。一晃20多年过去,我再没有踏上那片土地,也不知道那对学艺的表兄弟,是不是真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