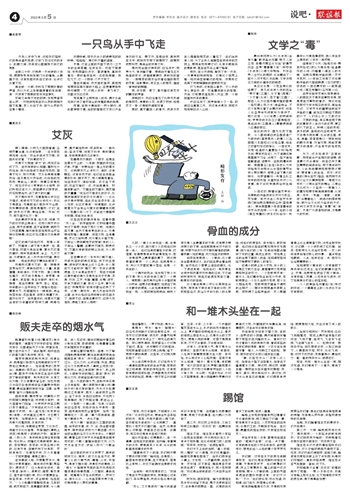和一堆木头坐在一起
雨山
■雨山
堆在墙根儿,一声不吭的,是木头。
是槐木?枣木?榆木?梧桐木?已经无法判断它们的出身和名字。这缘于它们被肢解,被风吹,被暑气和寒气浸润,被岁月染上了一种无名的黑灰色。可以想象得到,老鼠曾经从它们身下钻过,甚至一点点啃咬它们的躯体,鸡和麻雀曾经在它们身上踩踏,留下一层层干硬的粪便。这些年,它们用沉默战胜了一切。
木头在沉默中老去,它们在月光下一遍遍地回想当年的生命历程,那样的站立和伸展,那样的绿和生机,还有那样有趣的四季轮回,仿佛都是无法用年轮书写的秘密,更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甜蜜。五年,十年,二十年……冬夜里的雪花落在木头上,秋夜的白月光躺在木头上,夏夜里的虫鸣贴在木头上,春夜的细雨丝洒在木头上,这是木头的文艺范儿,更是小院的诗意。你若不是拥有孤独,万万不会看到,不会感受到。
没有火,没有烟火气,是不是木头的幸运?答案只有木头知道。或者说,从灶房不再需要用草木生火那一年开始,木头有过什么心路历程?答案只有木头知道。“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宋代欧阳修在《秋声赋》里用草木做陪衬,劝万物之中最有灵性的人少忧少争少怨。木头呢?无语亦无欲,它们从不招惹是非,是小院里最朴素最内敛最通达之物,只管随时光缓慢流淌,缓慢腐朽,对生命好似早有彻悟。
我在新年与旧年交替之际,在故乡,在熟悉的小院里,偶然间看到东墙根下那些似在沉睡的木头。看到它们我才看到久远的袅袅炊烟,看到年轻的母亲忙碌的身影,看到一个孩子在灶房里守着一堆火,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原来,美好的记忆也可以储存在这里。
“瞧,这些烂木头!”没有人这么说。除非他十指不沾阳春水,除非他不懂得草木之美。种过树,爬过树,亲眼目睹一棵树在木匠手里变成橱柜、床、凳子、桌子,用木柴烧过火,做过饭,我对木头有自己的理解,它们同样有灵性,即便是和大地、天空没有了深入的联系。
人生到处知何似?苏东坡说:应似飞鸿踏雪泥。那泥上偶然留有指爪的印迹,飞鸿不管,继续飞,飞往东飞往西,飞往南飞往北。从一粒种子或一根枝条开始,到扎根或迁移,从挺立到倒下,从潮湿到干枯,树木,也似飞鸿一般,成材不成材的,变换着身份,最后成为一截一截的废弃木头,装满记忆。
现在,我和一堆木头坐在一起,相对无语,我们等待下一个春天,等待下一个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