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解构乡村世俗的风情画
——读长篇小说《村支书》
胡堡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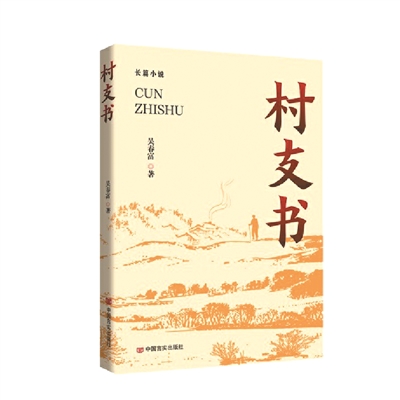 |
胡堡冬
曾经,读过吴春富先生的小说《老街》和《生产队长》,最近又读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村支书》(中国言实出版社),可以视为他创作的村镇小说三部曲。读过以后,感慨颇多,笔者想就这部小说谈一点个人的感受。
解构乡村,村支书是把钥匙。中国的乡村,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伴随着现代城市的经济发展,一部分农民们抛家舍业来到城里打工,他们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处于流动状态,他们农忙时回农村,农闲就进城打工;还有一些人只能在家种田度日。于是乎,我们看到农村人口、农村经济、农业结构,以及传统的农耕文化,在时代变化中引发了碰撞,并带来农村社会的一场变革。
吴春富的小说《村支书》从瓦窑村的窑厂承包切入,原村书记六喜将村窑厂承包给舅老爷,徇私舞弊,吃吃喝喝,导致村集体亏空。此外,六喜生活作风不检点,与二憨子老婆翠萍乱搞男女关系,二憨子敢怒不敢言,村民对六喜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大虎出头打了六喜,这种性格描写,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依据。最终乡纪委介入调查,决定撤换六喜,让村民李先泽担任瓦窑村委书记。李先泽见多识广,为人正派,他上任后不负众望,发包窑厂、维修村部、租赁水库、整修道路,改善了经济状况。应该说,农村题材的小说大多都脱离不了这样的窠臼,但作家吴春富所选取的角度和故事的结构方法,则另辟蹊径。他着重于人物和典型事件,以村支书作为小说的主角——因为村支书与乡和县有着直接联系,党的各项农村政策和指示都在村一级落实执行,可谓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此外,村支书与千家万户直接关联,可以说,村支书是直通民情的一把钥匙,其人品、素质、工作能力和重大抉择都会对百姓产生一定的影响。
吴春富正是抓住了这把钥匙,使小说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令人感叹。
鲜活的小人物,让小说熠熠生辉。翻译家主万翻译的《小说鉴赏》(中国青年出版社)中指出:“我们倾向于注意‘有个性’的人物,虽则他在很多方面看上去都很平常。如果没有个性的人物在作品里占着主导地位,那么这篇作品也许称之为传说或者寓言更为恰当些。”翻开《村支书》这部小说,你会发现其中的人物各具神采,六喜胆大妄为,油子刁钻油滑,二憨子懦弱无能,副乡长钱进朝一副官油子样儿,乡党委书记工作经验丰富、驾驭能力强等等。
读吴春富的小说,你能感受到他的深刻和对生活的观察细致。油子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他机灵、包打听、见风使舵,谈不上什么大坏,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油子陪李先泽到财政局见徐主任时,被写得活灵活现。油子根本不熟悉徐主任,只是在一次饭局上见过一面,但他能黏上去,硬是把关系拉起来。这样的人物具有普通性和典型性,就像一碗肉汤里的油珠子,虽然算不上什么,却是十分扎眼。
《村支书》中塑造的乡组委王新历,正派、客观、公正,在关键时刻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有原则,守法度,人物有血有肉,丝毫不感到生硬。在王新历身上你能看到许多在基层默默工作的干部的影子。
村妇联主任湘绣则是另外一种形象,她美丽端庄,是乡村经常可见的那种工作经验不足,却十分听话的村干部。由于她与财政局的徐主任是同学,徐主任曾经追求过她,油子利用这一点邀徐主任来村里坐客,想替村里要点钱,于是,便安排在湘绣家吃饭。应该说,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也可以看到另一面,即“人性之恶”,就是利用徐主任对湘绣的情感,从而导致湘绣“躺枪”。作家对人物的把握符合个性,符合逻辑。
世俗的乡村,永远是一片风景。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中这样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乡村也是世俗的。不是吗?乡村里的人和事、民俗中的礼尚往来,哪一件不纠缠在人情世俗之中?李先泽找徐主任想为村里要点钱,将家里的鸡蛋带上五十个,这不是有意去行贿,而是乡规习俗,带点东西好搭话,以免除陌生与尴尬。
瓦窑村大虎老婆去世了,“李先泽脚步厚实地走在前面,他面容肃穆,后面紧跟着湘绣、油子与小张文书。油子手里托着一挂万响的鞭炮——这是瓦窑村的规矩”。这段文字可以读出这么几个信息:一是村干部都来了,是给大虎面子;二是带来鞭炮,这是礼节。乡村的约定俗成,在乡下人看来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又如,翠萍嫁给二憨,二憨妹妹嫁给翠萍弟弟,这种换亲的婚姻在农村也比较常见。作家就是在这样的乡村风情画里,为我们编织出了《村支书》这部小说。
世俗是乡村的底色,我们寻着小说的章节,品味乡村与乡情,品味着那些鲜活的人物,或许你就懂得了那片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