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遥远,总亮故乡
——读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月光不是光》
张晓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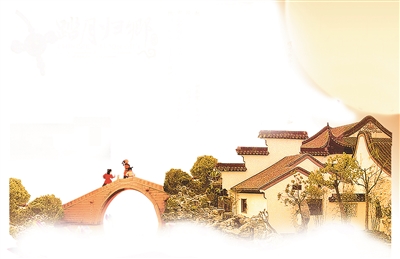 |
张晓飞
文学是土地和故乡的呐喊。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月光不是光》,是作家陈仓带领我们回乡。
塔尔坪,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没有通固定电话和手机信号;至今仍是土炕;每家每户的大门上都会有几条缝,最多的用处是被卸下来杀猪……这样的村庄在我们的土地上太多了,在经济发展的数十年间,在短视频如繁花烂漫的当下,少有书本为它们留下任何片段。当我读完全书,看到“如今,塔尔坪这个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小山村,被许多人所熟知了”跃出纸上,由衷感到欣慰与荣耀。山大沟深的塔尔坪,从此与鲁迅的鲁镇或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下。
伦理是艺术的内核,罗中立的名画如果不叫《父亲》,动人的共情便势弱了。伏案书写亲情几乎也是优秀作家的公共姿势,《月光不是光》书写的是亲人,主要是父亲。作家陈仓说,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是用肉皮熬出来的,是父亲活出来的。父亲陈先发没有像样的碑,作家把这本书当成父亲的碑,其中的千言万语都是父亲的墓志铭。
《父亲的风月》一篇写父亲进城生活的经历。这一定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儿子陈元喜种地、放牛、烧炭、淘金,吃过树皮草根、身怀劁猪骟牛之挤,自身努力加上一路贵人相助,在大城市上海扎下根来,成长为作家陈仓,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我有好多年没有捧着一本如此深情的书而放声笑过了。在我个人的阅读体验里,这一篇章的阅读享受超越刘姥姥进大观园。老爹看到青釉刻花瓷瓶,问是水缸吗?怎么挑起来?作家被老爹这么推着,说有些人喜欢把水扛在肩上,说可以去小卖部打酱油,越说越扭曲,越说越离谱,还不如干脆告诉爹这就是个摆设而已。老爹乘电梯,紧张地瞄一瞄,被时光隧道似的那些情景吓得不轻,一个丫头从一楼进去再从十四楼出来变成了一个老太太。这些戏剧化的叙述,有精巧的结构,有灵动的节奏,有声音,有画面,有特效,让我一次次笑出泪来。
当读到儿子开车带老爹跨越东海大桥,驶进辽阔的海面。我知道心要被刺痛了,我读懂了世间的孤独。老爹要回去了,坐上了火车,在一个粉红女孩的照顾下,远行返乡。柔软的女孩吃力地帮他放行李架时,三个高个子的年轻男人在熟视无睹中继续聊着天。塔尔坪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有树林,有溪流,有成群的锦鸡、老鹰、野羊、麂子、獐子、果子狸。它们与他平等地行走于天地之间,鸟会落在他的肩头,雪会下在他的身后,他能听懂一草一木的话,塔尔坪的春秋和自然是他一辈子与万物共用的语言。老爹不会再来了。
老爹回去后,独自准备着自己的后事。半夜三更睡不着,就喂喂老鼠,试试寿衣,躺在棺材里睡一睡。这是作家的惊人之笔,搅动着天下子女的五脏六腑。《拯救老父亲》一篇写抢救父亲,是教科书,是戳人心魂的孝感动天。老爹又活了几年,在一个小雪节气与世长辞。那一刻,我闭上眼,想起余华《活着》里写的那句“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合上书本的时候,我闪出一念:唐代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第八届鲁奖获奖作家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对应关系呢?仙是大湖上与候鸟、江豚相伴的沈念,圣是煤油灯下煮鸡蛋的小先生庞余亮,佛是把善良、智慧和爱撒向人间的陈仓。剃着光头却无戒疤、未入佛门却一心从善的作家陈仓,已经用他的文字建起一座神圣的庙了,在纸上的塔尔坪。
月光和爱,洒满故乡,也盈在读者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