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桥,渡人渡己
——读周华诚《流水辞》有感
郑凌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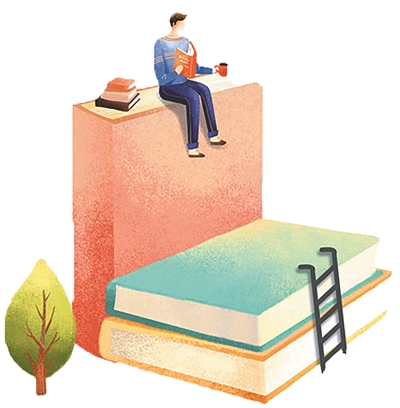 |
郑凌红
在春天的某个路口,天空微雨,遇见了《流水辞》。在文字的世界里,我用十天的时间,完成了个人的解读和一次次的怦然心动。如果一定要给这本书一个最大的注解,在我的字典里,是“渡人如渡己”的悟。
喜欢诗意的人,也喜欢诗意的书。未曾谋面的《流水辞》在我想见之前就热闹开了,恰如难得一见的华诚兄一样,让我不紧张却颇有触动。人和字是可以对应的,文字里是一个人最大的精神世界,这世界由阅读、阅历、悦己、博爱等版图构成,带给受众斑斓的想象,可以参禅,也可以悟道,最终抵达“书人合一”的快意,天朗气清的境界。悟道被很多人追求和向往,而“悟”和“道”是连在一起的。先有独特的感悟,才能遇见自己理解的“道”。道路千万条,一次次地走进文字,是解读的密钥。在《流水辞》里,道的载体就是桥,九个章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九曲回肠,曼妙生姿,带给你一段段隐秘之美,却又带给你时时放心不下的思考。
泰顺的古廊桥,是一个放不下的话题。有沧桑之美,也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经由人演绎,故事经由妙笔而耐人寻味。作者在遇桥、寻桥、读桥、解桥、架桥等架构中,构建了儒、释、道完美融合的“大隐之道”。儒是正统的元神归位,泰顺廊桥被人知,却又不被人知。如果少了作者被“点将”,被带着一颗“解剖麻雀”的心往返于那片山水,那些人事,那些桥与桥之间的断层和裂缝,那么那一座座桥也许也只是一座座桥,即使“每一页都写满故园风雨”,却很难通向它所期待的明天。我在阅读的时候,感慨于作者广阔的视野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一种难得。广阔的视野,具体表现在对桥的厚度和广度的拓展。《旧时光》里的薛宅桥,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性,承受过命运的苦厄,依然仰首挺胸,不屈不挠。《桥头的茶馆》里面的北涧桥,在双贵的话匣子里有了太多的画面感和历史纵深度,桥边人家的生活和文物保护的现实困境都一一摊开,也为泰顺人的“三杯香”和“廊桥红”打了广告,当然更多的是他乡如故乡的期待。我相信,每位作家在走进一个地方之后,会更多地关注“物外”的世界,而文字的表现,能通过不同的解读带来回响。桥梁学者,文保专家,非遗传承人,地方官员,旅游策划者,当地乡民,都有不同的遗憾,不同的品读,不同的期待,也能发挥不同的力量。
也许一本好书,不应该只有美感,而应该是带给人更多的思考,甚至是思考之后所能产生的微妙变化。也许,这变化需要时间的加持,但不妨碍它在时光里散发的芬芳。显然,《流水辞》做到了。在书中,作者进退有度,虚实相间,似快则慢,似表实里,起承转合,自然流畅。一些浑然天成、信手拈来的字句,展现的是哲学之思、哲学之光。如“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生活,在别人眼里,就是时间最珍贵的美呢”,这显然是对众生的提问和自省,也由此把廊桥的现在与未来进行了“无缝衔接”,这个衔接既是廊桥本身,也是廊桥内外的每一个人。又如,对“董直机”的描述,从13岁到17岁,到24岁,到79岁,一颗匠心连同“人生里那些高光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被重新打开,绽放光芒”一起,余音袅袅,绵而不绝。
桥不仅仅是桥。桥是人们的依托和信仰。书中用看似柔和的字眼,道出了桥对于泰顺人的非同寻常,以及跳出“桥”去看“桥”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在正本清源的同时,抛弃了旧眼光,打开了新格局,树立了心风向。修建桥梁,渡人于川涧;布施施惠,渡人于贫穷;改恶修善,渡人于苦难;勤学好问,渡人于愚钝;修行学道,则是渡人超脱生死。桥是一道道光,照见每一个阅读它的人,也照见它自己的落寞与孤寂,徘徊与梦想。梦想是包医生和陈医生,梦想是双贵,素秋,尤静静,曾家快,季海波,吴学养,周善灵,李晓娟,也是不知名的老妪,背着竹篓从廊桥走过的采茶人,钟晓波……或许最大的梦想是作者笔下的“二禾君”,因为文末的“二禾君,你也要来看廊桥吗?我在廊桥等你”,让读者的思绪飘向了更遥远的星空。
在泰顺,有多少桥,就有多少故事。有多少故事,就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被铭记的或是被带上路的食粮。修桥、看桥、过桥,我们都是桥上的风景。写桥、感桥、连桥,作者便是桥上的引路人。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作者是内外联通的。既向内求,又向外走。向内求得关于桥的种种“真经”,向外求的是桥的现实“破题”,幻化出惺惺相惜,穿越时空的力量。除此之外,感人的弦外之音或许是作者的虔诚,虔诚地走进廊桥,走进那里的人,感恩路上的遇见,关于那些,在文中,在字里行间都可以找到不同的谢意、祝福、期待和回味。我相信,这是一个男人最隐秘的力量,也是一个作家最淳朴的发光体。因为,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感悟,既发于你的心,落于你的笔,也来自于山川湖海的遇见,一见如故的缘分。
《流水辞》是一座桥,渡了很多人,但它不刻意。不管你来与不来,它都在那里等你。因为,人生如寄,渡人如渡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