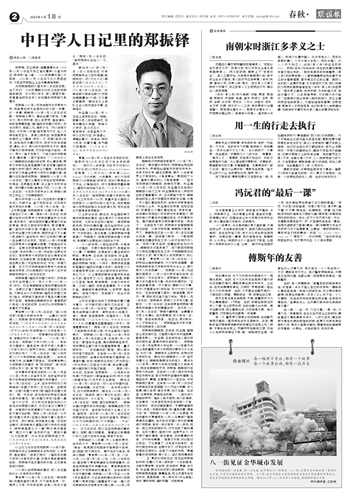中日学人日记里的郑振铎
周维强
 |
| 郑振铎 |
□周维强
郑振铎,笔名西谛,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盐公堂”。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1958年10月18日率文化代表团出访,飞机在苏联喀山上空失事遇难殉职。
与郑振铎同时代诸多学人日记的记载,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清晰也比较立体的郑振铎的面貌。兹分别以学术、接人等若干面,来看看当时中日学人日记里的郑振铎及其著述。
郑振铎1935年2月被迫离开北平燕京大学,可能是他学术生涯中比较大的一件事。这一件事,顾颉刚1934年6月25日日记记载:“郑振铎系燕大、清华合聘之教授,又兼北大、师大两校课,而心目萦萦,惟在得钱。到故宫搜集图画,编《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先发行预约,每部二元,得数千元。然以彼绝不用功,只抄别人成编,稍变排列方式,他人之误未能改正也。其第二册先出,吴世昌摭其中常识上之错误,写成一文,投寄《新月》杂志,出版后送与雷川校长,故校长拟将彼辞退,清华、北大、师大中对彼印象亦不好,谓其不解平仄而讲诗词,对好的作品只能说:‘伟大!伟大!’皆不支持之。乃彼又在校中掀起波浪,真所谓‘人苦不自知也’!”(《顾颉刚日记》)顾颉刚日记里这段记录,核心事件是,燕京大学研究生吴世昌撰文批评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若干“常识上之错误”,发表出来的书评又被拿给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看,吴雷川遂拟辞退郑振铎。顾颉刚1934年12月23日日记:“国文系高年级学生欲驱郑振铎,叶楚生、王锡昌主其事,将上呈文与校中当局。郑行事太无赖,宜有此下场。”1935年1月11日日记:“今日执行委员会议决,振铎以研究工作名义,下学期即离校。”
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出版的《吴雷川日记》,残缺不全,留下来的日记,没见有片言只字说这件事。1933年2月26日有一条:“上午郭绍虞、郑振铎同来,谈国文学系事。”没有记谈了什么事。同年8月2日日记,收进雷川在杭州致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务长的信,其中有云:“前日接到校董会惠信及先生的复信,昨日又接到学校聘书,敬悉壹是。鄙人辞去校长职务者,校董会允准,并仍请返校专任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先生又不允鄙人取消前约,留住杭州,就之江学院之聘,鄙人自当遵约仍返本校。”可知1933年8月吴雷川已获燕京大学董事会同意,不再担任校长职务。容庚与郑振铎同在燕京大学国文学系任教,中华书局2019年5月出版《容庚北平日记》,其中燕京大学时的日记也偶有记郑振铎的,比如餐叙等,吴世昌和容庚走得近,但容庚这部公开出版的日记,亦无一字道及此事。本文不对郑振铎离开燕京大学前后原委作考索,仅比照同时代中日学人关于郑振铎学问和为人的日记记述。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初版由北平朴社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1932年12月)印行。朴社是顾颉刚主持的民营出版机构。如果仅仅看了顾颉刚日记里的这几段话,大概率会以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拙劣,郑振铎不惟学问不堪且行事无赖而不自知。稍稍跳出顾颉刚日记,看看同时代其他人日记的记录,也许对认识郑振铎及其著述不无裨益。
夏承焘1927年12月4日日记:“阅《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台静农《宋初词人》、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皆可浏览。”(《夏承焘日记全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版),1928年3月25日日记:“灯下以《宋史》校郑振铎之《文学年表》(即《中国文学年表》)……郑君谓成此时日甚匆促,有暇欲校补为单行本……”1929年1月3日日记:“郑振铎《文学大纲》二本……其叙述外国部分,据其自序,取材于西人所著之《文学大纲》及《世界文学史》,中国部分亦叙述多而论列少。”9月14日日记:“阅《小说月报》二六六号郑振铎《词的启源》……余所见郑君文字,此篇最不苟者矣。”可知夏承焘以为郑振铎文学著述,有“可浏览的”,有“叙述多而论列少”的,有“苟”有“不苟”的。
日本青年学者目加田诚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受公派留学北平,他的留学日记数次记录阅读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著述。1933年11月2日日记:“上午,在东安市场买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五元五角),当即读起。”这部《中国文学史》即《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同一天日记,目加田诚记录自己阅读这部书的意见:“读《中国文学史》至第八章一百六十三页。迄今所见作者的见识以及其观点中赞同处颇多,不过仍有实力薄弱之感。许是郑氏学问得意处乃宋以后俗文学,故不得不如此吧。”同年11月5日日记:“今天读《中国文学史》至第三卷四十章七百四十五页迄。时代愈降,郑说愈有价值。”日记的注解云:郑说愈有价值指这部文学史北宋部分,特别是指第三十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第三十九章“话本的产生”、第四十章“戏文的起源”,均论述此时期民间文艺。(《目加田诚北平日记》汉译本,凤凰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以上这几条日记可知即使1934年之前,郑振铎亦未必如顾颉刚日记所说的“心目萦萦,惟在得钱”“彼绝不用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的价值,识者还是能看得明白的。郑振铎对自己著述的长短,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934年以后郑振铎的著述,时人日记里的谈论,也有可资参考的:
夏承焘1940年5月23日日记:“假郑振铎《中国版画史》样本,灯下阅其自序一过,搜罗二十年,引书数百种,此前人所未为者也。”同年9月13日日记:“阅郑西谛论梁任公一文,甚好。”
顾廷龙1947年2月3日、4日21日的日记,均有郑振铎来合众图书馆借《新西域记》、还《文化大系》等的记录(《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1951年6月24日日记:“送单伯钟及西谛见假之《支那古铜器菁华》六册,交文管会谢稚柳。”顾廷龙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主持馆务。
叶圣陶1948年1月10日在上海写的日记:“傍晚,同事十数人共往振铎家,观其所藏古代明器。振铎为之讲述,自汉迄五代,一一言其特点,与其鉴别之方,并以实物为证,听者惬心。渠嗜此事才一年有余,而识力极丰,收藏亦富,其气魄大可佩服。”(《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
夏鼐1949年4月18日在北平写的日记:“阅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李氏为人类学者,然此书不过将《仪礼》与《礼记》二书依Wissler,Man and Culture[威斯勒:《人与文化》]中所谓Culture Scheme[文化体制],分类摘录。余以为如郑西谛之《汤祷新释》的写法,将近代野蛮社会之风俗,以解释旧礼,远为有趣味而富新意义,惜李氏尚未能及此也。”(《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1958年2月20日日记:“阅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卷下,这三本书共1388页,其重点在戏曲和小说两部分,以新材料的介绍为主,走的是胡适小说考证的路线与他的演化观,郑先生在这方面是有其贡献的。”
以上数条日记,顾廷龙、叶圣陶的虽不是说郑振铎的著述,但也是涉及了郑的读书和学问。这数条日记可以推知:一是郑振铎做学问,材料收集极富,在充裕的材料上发挥其见解;二是郑振铎做学问,眼界开阔,取材、方法和结论,每多新意;三是郑振铎涉猎面甚广,气魄甚大;四是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其得意处主要在宋以降的俗文学。
一个人的学问,从起始到成熟,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只要不是投机取巧,而是能努力从事,广搜博取,总是能够从青涩进到成熟的。夏承焘、王伯祥、目加田诚、叶圣陶、夏鼐等中日学人1927年至1958年日记记述里的郑振铎,可做一个例子。即使被吴世昌所指摘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其可取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这部书所收的材料,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同时期其他著作所未能论及的,诸如变文、戏文、诸宫调、散曲、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这部文学史还第一次附入插图,图版且甚精美,不少还是珍品。顾颉刚所谓郑振铎“心目萦萦,惟在得钱”“彼绝不用功”,恐怕是不一定合乎郑振铎的实际了。
上引日记里也说到了郑振铎收藏之富与着力。这方面还可以再引几条日记。王伯祥1926年3月13日日记:“看《续金瓶梅》,是书由振铎处假来。渠聚旧刊小说甚多。演义、弹词、宝卷等俱夥,将编目示人,予甚赞其成耳。”(《王伯祥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6月版)收藏富有且整理编目公开予人,可谓嘉惠学林了。同年4月27日日记,郑振铎“又新购明刻传奇二种,予与圣陶观之皆叹贵云”。郑振铎1927年5月至1928年5月旅居英法,6月8日返回上海,王伯祥6月15日日记:“散馆后与圣陶、调孚同振铎至其家,观所携归名画及邦贝古壁画摄影等。量多而质好……”日记里说的“散馆”,即从商务印书馆下班出来。王伯祥1940年8月8日日记与何柄松、徐调孚到郑振铎家看振铎“近得诸珍籍:宋本《吴郡图经续记》《严州图经》《严州续志》《五臣注文选》等,其他黄尧圃、顾千里校跋之书指不胜屈……”。同年9月8日日记,王伯祥“往振铎所……纵观其近日所得《万历疏钞》《乾隆谕旨条例》并外交部《四国专档》及关于矿务各原档”。顾廷龙1940年3月3日日记:“廿七日过中国书店,见《辛斋诗稿》,补记于此……此书索价四十元,已为郑振铎要去。”顾廷龙1944年10月3日日记:“西谛来,提及《袁双秋日记》,渠云前年底已付一千七百元……”叶圣陶1947年4月4日日记:“傍晚,诸友至振铎家……振铎近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颇搜集古物及艺术品之印本。室中陈列中古之土俑二三十件,皆可观。”宋云彬1951年4月21日日记记郑振铎和他在杭州“至旧书店看书,振铎以七十万元购得初刻《六十种曲》……大乐”(《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这几条日记,可以见出郑振铎收藏的眼力、视野、魄力和勤勉。建基在这样博闻广识之上的文史学术作品,焉有不足观?
郑振铎的个人收藏,予人也是极豪爽,出手极大方。夏承焘1938年11月13日记:“早徐一帆邀同过郑西谛于庙弄四十四号,出《楚辞》数十种见示。谓予如欲为新注,可举以相假。”夏承焘1940年12月1日、15日、29日,1941年1月2日、12日、19日、22日的日记,都记载了夏承焘借或还郑振铎藏书,还有在郑振铎家钞录藏书的。夏承焘做研究曾得力于郑振铎的收藏甚多。王伯祥研究太平天国史事,郑振铎1927年5月至1928年5月旅居英法,为王伯祥购得近世史料《中西纪事》《豫军纪略》《盾墨留芬》《能一编》《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等七种,1928年2月寄回上海给王伯祥用。
顾颉刚对郑振铎恶感甚烈,1950年7月1日日记:“闻中国科学院中,郑振铎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罗常培任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去年予到北京,晤王日蔚君,渠云:从此教育界上不再有钩心斗角者事矣!哪知到了今日,偏是这辈会钩心斗角者得意……”但反观郑振铎对顾颉刚,则胸无芥蒂。叶圣陶1953年12月22日日记,叶圣陶与王伯祥谈顾颉刚今后之工作,叶圣陶是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王与顾皆为老友,顾颉刚当时在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做总经理,这是一家小型私营出版机构,出版科学教育挂图及史地小丛书。叶圣陶日记写道:他和王伯祥“共谓若今之搞私营出版社,殊非所宜。伯祥谓科学院古代历史研究所有意招之,振铎并告以我署将设古籍出版社,亦拟请其参加。据云颉刚曾表示明年暑中可择一而往之”。沧桑巨变之时,郑振铎亦在替顾颉刚谋划出路。这样对照来看,顾颉刚反显得小气了。顾颉刚自己在1956年7月2日日记里也记有一事:“伯祥偕乃乾来……乃乾由振铎调至古籍出版社工作,从此该社有内行人矣。”说陈乃乾未至时,古籍出版社无内行人,顾颉刚亦过甚其词了。陈乃乾因郑振铎之力而至古籍出版社工作,不知顾颉刚日记写到这儿时,是不是还认定郑振铎为“钩心斗角者”。夏承焘1957年3月9日日记:“二时张白山偕陈翔鹤来,为文学所组稿事。谓郑西谛前旬在文学研究所所务会议上,提及邀予入科学院事……”郑振铎1927年5月出国旅居英法,10月24日伦敦致信王伯祥,王伯祥这一天日记有云:“读振铎书,谆谆以从事太平天国专史为勖,并许我助搜材料。”王伯祥接着写道:“予大感动,懒筋为之大震。拟于《天国革命史》写毕后,努力为专门之研究也。”王伯祥接着又感叹:“铎信甚勤,而予只一复,即此可见奋不奋之判矣。”同年11月1日日记:“接振铎书,殷殷以太平史为勖,至感动。”11月3日日记:王伯祥复信郑振铎“谢激励并商榷太平史撰著体例”。宋云彬1951年4月21日日记:“振铎为唐弢言:‘余最喜与云彬小饮清谈,彼风度萧洒,数十年如一日,不若一般自命前进者,一脸正经,满口教条,令人不可向迩也。’。”郑振铎品评云彬风度,亦可见振铎本人的风度。
郑振铎和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曾同在上海发起朴社,又曾同为商务印书馆同事,都是老熟人。叶圣陶、王伯祥先后从商务转到开明书店,都是开明书店的老人。郑振铎1931年9月至燕京大学任教,1935年春天返回上海做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系主任,长达6年。顾颉刚北上做教授,主持迁到北京的朴社。顾廷龙比顾颉刚小11岁,但家族辈分上,顾颉刚是顾廷龙的侄儿。顾廷龙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读研究生,就住在顾颉刚家中,郑振铎、顾颉刚均在燕京大学任教。王伯祥1932年从商务印书馆转至开明书店,做过开明书店编译所编辑、经理室秘书、襄理、总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与郑振铎相交甚深。王伯祥1940年5月12日日记云振铎在动乱世道里“为公家出力购藏,资力既厚,魄力自伟,南北书贾,归之如壑。他日者,石渠录勋,振铎自当标首……”,但也说及振铎的弱项:“惟此公疏于接物,或以此得谤,亦在意中。”这或者可视作王伯祥知人之言。王伯祥这一则日记里接着说:“予谓毁誉固可不计,独有八字面致铮规,则‘谨其收藏,慎其交际’耳。”郑振铎1958年10月18日遇难,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同年10月20日晨间广播新闻得悉此噩耗,当天的日记里以很长的篇幅追忆郑振铎,其中一段这样写:“这八年来,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较长,对于他的了解较清楚。他好大喜功,粗枝大叶,但是气派大,对政策了解较清楚,有纪律性,决定事情较迅速。对于所中事情,一般是不干预,我们做过汇报他一下也便算了,没有很多的争执。自尹达同志来所后,他更放手了,对考古所与文物局的互相关系,他起了沟通的作用。”夏鼐接着还说郑振铎“是个忙人,但仍有闲情逸致……”。王、夏的这两段日记,可见出郑振铎的学问、收藏以及待人接物的一个总的面貌,与前引夏承焘、王伯祥、目加田诚、夏鼐、宋云彬、叶圣陶、顾廷龙日记可以前后映照。我看郑振铎相貌堂堂,高鼻隆准,和上述诸先生日记所述,甚是相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有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