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夏传经的读书故事
唐宝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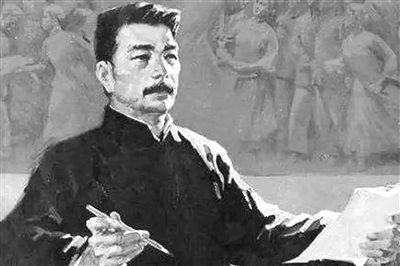 |
| 鲁迅画像 |
□唐宝民
胡适与买饼小贩袁瓞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了,人们感慨于胡适这样一个大学者能以平等的姿态对待袁瓞这样一个卖浆引流者。其实,鲁迅先生对待小人物,也是极为尊重和热心的,比如,夏传经就是一个受到过鲁迅以礼相待并热心帮助的人。
查鲁迅1936年的日记,曾经有八次提到了“夏传经”这个人,分别是2月19日、2月24日、2月29日、3月2日、3月11日、3月12日、4月1日、7月8日(见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从日记的记载可以知道,鲁迅先生第一次收到夏传经的信,是在1936年2月19日:“十九日,小雨。午后得夏传经信,即复。”鲁迅收到信的当天,即给夏传经回了信。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天后的日记中,鲁迅又写到了夏传经:“二十四日,寄夏传经信并书四本。”也就是说,鲁迅在24日那天,不但给夏传经写了信,还给他寄了四本书。那么,夏传经到底是什么人,值得鲁迅如此关切他?在《鲁迅全集》第十七卷第190页,笔者查到了关于夏传经的人物注释:夏传经是南京盛记布庄的一名普通职员,曾经写信向鲁迅询问著译的有关情况及研究文学的方法。
关于夏传经与鲁迅交往的事,夏传经曾经向许广平做过介绍,据夏传经讲,他给鲁迅写的第一封信,是向鲁迅请教一些读书方面的问题的:“这信的内容,是问先生《竖琴》的前记和《野草》的序诗,怎么在最近出版的原书里没有了,以及怎样研究文学,并说了一些我读《伪自由书》的感想,说是,我简直不拿它(《伪自由书》)当文学书看了,这是一本很好的预言书。又抄了些我读过的先生的著译,问先生还有什么书未读到的,请先生告诉我。”鲁迅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就给夏传经做了回复,这封回信收在了《鲁迅全集》第十四卷第32页上:“《竖琴》的前记,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的,去年上海有这么一个机关,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直到杜重远的《新生》事件,被日本所指摘,这才暗暗撤销。《野草》的序文,想亦如此,我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高尔基文集》非我所译,系书店乱登广告,此书不久当有好译本出版,颇可观。《艺术论》等久不印,无从购买。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关于研究文学的事,真是头绪纷繁,无从说起;外国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国,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这并不难,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常常看书,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经历一多,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我的预测时时有验,只不过由此一端,但近来文网日益,虽有所感,也不能和读者相见了。”在信的后面,鲁迅还为夏传经开列了一些书目,有25种之多,鲁迅还在书目的后面对所开列的书目进行了简单的点评。夏传经说:“这上面的书,都是我那时不曾读过的。”夏传经收到鲁迅先生的亲笔信后,非常感动,感动于一个著名作家能在百忙之中回复他这样一个普通读者的信。
而更让人感动的事还在后面,几天后,夏传经又收到了一封鲁迅的来信,这封信就是鲁迅于2月24日写的那封,这封回信收在了《鲁迅全集》第十四卷第39页上,信中说:“顷偶翻书箱,见有三种存书,为先生所缺,因系自著,毫无用处,不过以饱蟫蠹,又《竖琴》近出第四版,以文网稍疏,书店已将序文补入,送来一册,自亦无用,已于上午托书店寄上,谨以奉赠。此在我皆无用之物,毫无所损,务乞勿将书款寄下,至祷至祷。”也就是说,鲁迅先生给夏传经寄了四本书。夏传经当然更加感动:“这封来信,真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先生赠了我这么许多书。于是我便注意着邮差:一次一次地过去了,却总不见寄书来!这时我的心里真难过极了,又不知道先生是送我几本什么书,又怕被邮局扣留,在这种心情下,熬过了一夜,在第二天的中午才收到书,赶忙拆开一看,才知是《竖琴》《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坟》和两本《海燕》。”收到鲁迅先生寄来的书后,夏传经便认真阅读,并期望以后能更多地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然而,不久之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就病逝了,夏传经得知消息后异常悲痛,为了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怀念之情,他想珍藏一件鲁迅先生的照片或遗物,便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里,我还附带着一个请求:假如有鲁迅先生的生前照片的话,我想请夫人给我一二张,使我好留作一个纪念。但,假如没有,那就只得算了。如果有关于鲁迅死后的照片见赠一二张,我也同样地欢迎和感谢!但如果连这也没有,那么,即使是先生的只字片纸或者极不值钱的遗物给我一些,我也是非常感谢的!”
相对于鲁迅先生这样一个文学巨匠而言,布店职员夏传经的确只是一个小人物,但鲁迅先生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小人物而慢待他,而是依然待之以礼,不但及时给他回了信,还主动给他寄书,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仰望的精神境界。鲁迅先生对待小人物的态度,是建立在对小物的尊重和人格平等基础之上的,而恰恰在对待小人物的方式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伟大或者渺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