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偷读”岁月
刘群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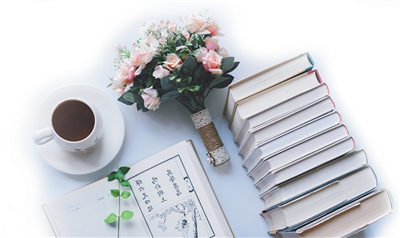 |
刘群芳
上世纪80年代,物质生活并不富裕,能解决温饱已经是较好的家庭,阅读则是一件奢侈的事,想读书而不得似乎是再正常不过。在提倡全民阅读的今天,每每忆及我的“偷读”岁月,充满幸福感。
小学三年级,我跟母亲一起去邻居二伯家玩,稍显拥挤的客厅里,大人们聊得热火朝天,我在一旁百无聊赖。忽然发现他们家桌子上有五六本杂志,我随手拿了一本《故事会》,没想到却被吸引了,临出门前,伯母见我喜欢便让我拿回家看,我高兴得不得了。剩下的内容很快被我读完,烦恼随之而来,就像吃了一顿美味的饭菜后突然什么食物也没有了,我面临着“断粮”,只好把手上的这本拿出来反复看,三四遍后对每个故事已烂熟于心,看到题目就可以把整个故事复述出来,有些句子都会背了。
我对新的《故事会》充满了期待,总想着怎样才能开口再借,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渴望。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下午,母亲让我拿着刚摘的橘子送给二伯家,推门却发现家里没人,我把橘子放在餐桌上,另一边的《故事会》仿佛在呼唤我,我环顾四周,没有任何人,顺手拿了最上面的那本,以最快的速度塞进腰间回家了。
我心一直在狂跳,毕竟这是“偷”来的。为了不让家里人发现,我把《故事会》放在衣柜的最里面,一有空就偷偷拿出来看,看完后再找机会换新的。次数多了总有露馅儿的时候。有一天,我正看得津津有味,二伯来我们家了,不料,他只是淡淡地说:“原来你喜欢看《故事会》,看完了去换吧,记得还回去就行。”我欣喜若狂,二伯家经济条件好,但小气也是出了名的,在借书这件事上居然可以这么大方!我开心得想跳起来。
有了二伯的“恩准”,我开始光明正大出入他们家,大半年的时间至少看了20本《故事会》,之后已不满足于读那些简短的故事,于是又找来了别的书。这也让我出现了幻觉,总认为学习之余只剩下看课外书这件事,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都要分担一些家务,看“闲书”的时间很少。有一天,我起床一头扎进书中,被跌宕起伏的情节深深吸引。猛然间,才想起还没有做早饭!于是,心急火燎地开始烧水、打扫卫生,还没进行到一半,母亲已经出现在我面前了,看我慌慌张张的样子,母亲责怪道:“你到底在忙什么?做事比乌龟还慢,长大了还能讨到饭吃吗?”面对母亲的责骂,我没有丝毫的不悦,相反心情还很好,一个早上的阅读换来几句责骂算什么呢,我在书中的天地间遨游,这种快乐又岂是别人能感受到的?课外阅读让我收获满满,作文总被老师当作范文,甚至偶有见报,从此以后,母亲不再责怪我看“闲书”了。
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泛滥,读书依旧是我最享受的事,手捧“闲书”静心阅读是最放松的时刻。比起人,书更简单、更丰富,也更能丰盈人的心灵。读书,其实也是读人。
就像一位老师所说:“我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
回忆起童年时“偷读”的时光,依稀还记得那些看过的内容,就像儿时吃过的饭菜,都化作了我成长的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