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年华识见真
——品李利忠《绝句新裁五百章》
尚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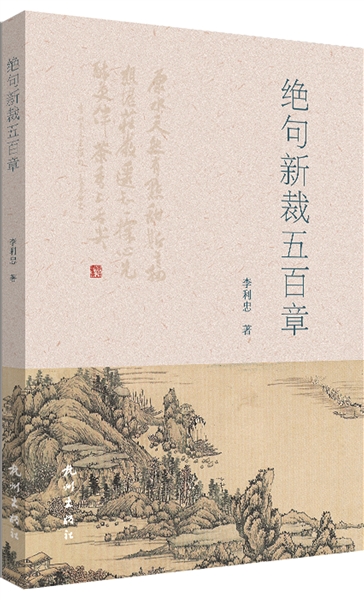 |
尚佐文
有个所谓的职场“潜规则”:永远不要和同事做朋友。我偏不信这个邪,在工作过的每个单位,都结交到了一些真朋友、好朋友。利忠是其中特别有才且极具个性的一位。
初见利忠,是在二十年前的某一天。此前已在网络上读到他的诗作,爱赏不置,于是和王翼奇先生一起到利忠供职的报社登门拜访。然后欣喜地发现,我和利忠不仅在旧体诗写作方面趣味相投、见解相似,而且都好杯中物,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了诗友兼酒友。有几年时间,我们经常于下班后在两个单位之间找家餐馆对酌。后来,我们在杭州共同的诗友兼酒友多了,变对酌为群饮;再后来又玩席上分韵,美其名曰“雅集”。东坡说“诗酒趁年华”,我们的中青年岁月因这些对酌和群饮、雅集,增添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酒是卸妆水,见人真性情。利忠平时是个略显腼腆的人,但几杯酒落肚,顿时拥有了放飞自我的资本,通常是以口头禅“我来说一下”发端,开始谈诗论史,兼及世态百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胜解纷呈。而他居家独酌,又是另一番古代名士范儿。我是属于“看菜喝酒”型的,在家吃饭,除非有中意的下酒菜才会小酌几杯,啤酒不过一瓶,白酒止于二两;利忠则是“汉书下酒”型,边读书看稿边细酌慢饮,一个晚上可以喝掉两三瓶绍兴黄酒。说起来我们酒量不相上下,但显然利忠喝酒比我更具文人风度。
利忠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在我认识的诗友中,他是少有的旧诗、新诗、散文都写得极好的多面手。他的旧诗,造语精准、语态自然,尤为可贵的是,不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他时常能透过表象直击本质,发人深思。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有才、学、识“三长”之说,其实不论治史还是创作乃至为人,“识”都是最重要的。“识”是识见,是洞察力,有了“识”,一个人才不至于迷失在纷繁复杂的世相和眼花缭乱的辞藻里。利忠的“识”尤其体现于他的散文。他出过一本散文集《是什么让我们嚎啕大哭》,我曾认真拜读过一遍,击节赞叹之余,也时时因文章的沉重和尖锐而感受到压迫与刺痛。利忠和我都生长于农村,出身草根。我倾向于过滤记忆,只愿意去回味和述说美好的、有趣的往事;利忠散文记录的一些经历、揭示的一些真相,会搅乱我风平浪静的意识河流,让沉潜于河底的一些晦暗的记忆和思绪翻涌上来,这实在不是愉快的阅读体验,以致我一直不忍再读。我不相信有世外桃源,但感觉世界之大,总有容纳身心的缝隙,因而在很多方面都习惯于做“逃兵”。和利忠相比,我是自愧不如的,不仅是他的才气,更有他这种直面过往与现实的勇气。利忠曾自述“我对自己文字的要求有两条,那就是别致和深刻”,这两条,在他的旧诗、新诗和散文中都做到了,前者得益于他的语感和才气,后者有赖于他的识见和勇气。
这篇文字,本是应利忠之命,为他的新书《绝句新裁五百章》作序。迁延多日,殊为愧恧。不过拖延症也并非一无是处,就在我延宕的过程中,我的另一位同事兼诗友酒友辣斋兄已经为此书作了一篇序言,不仅文辞精美,而且品评精到,题无剩义,无烦我再画蛇添足了。辣斋之文可谓直探骊珠,拙文则是在外围打转,按照孟子“知人论世”的教诲,拉杂写点对利忠之为人为文的印象与感触。
几年前,利忠曾赠我一诗,题为《与佐文兄饮酒感赋》:
昔年惭不识,今日聚仍频。
坐久杯盘罄,谈深海岳春。
浮生真草草,小酌倍津津。
渐老豪情在,相逢信有因。
前半叙聚饮情形,如在眼前;后半发浮生感慨,心有戚戚。去年重读,有感而次韵奉和,不避续貂之讥,附录于此:
重读利忠饮酒旧作忽思相识倏将廿载
幸诗酒之会未尝间断因次其韵奉和
廿年真一瞬,聚饮幸犹频。
妙笔千人敌,欢言四座春。
同倾步兵酒,莫问武陵津。
留取闲情在,须完未了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