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纸的字字珍重
——《听香集》后记
戴丽 唐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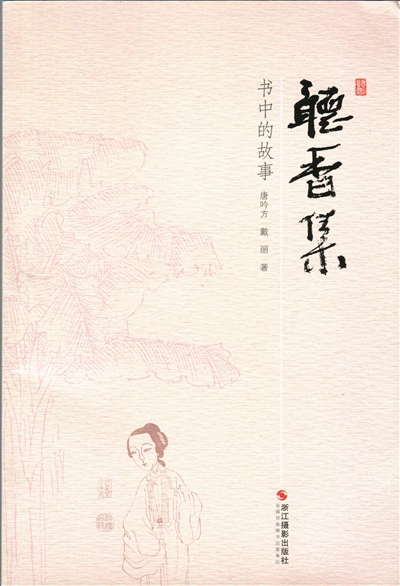 |
戴丽 唐吟方
这是一部借助故纸打捞嘉善历史文化细节的小书。之所以取这个书名,大概考虑到传承历史的香火总由故纸来承担。人们记录历史,刻书印书藏书,就是整个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一环。人寿不过百年,而书比人长寿。当你打开一本书,书不会说话,但会告诉你曾经发生的过去,于是就有人用“书香”来形容故纸的氤氲。是的,由文字垒成的书常常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味,阅读它们,会嗅到来自历史深处前贤的呼吸,传达和今天一样鲜活、多姿多彩的生活信息。
“听香”是二位作者俯身故纸身影的写照。当然,“听香”之名也和二位作者有瓜葛的香湖有关。戴丽从小生活在香湖之滨,她对地方文史的兴趣从这个流过古今的香湖开始;唐吟方曾在香湖之畔有过不短的嬉戏生活经历。“听香”是倾听历史的回响,也是二位倾听者卑微的记录,希望由他们的工作,重现故纸背后人物的清风明月。
投身时光中的故纸,二位作者常常惶恐不安。小心翼翼地过滤落入眼帘的每一行字,再三斟酌,反复比对,怕误读也怕解读过度。那情景有点像乞丐托钵沿街乞讨,又似冬夜剔炉柴的取暖者,唯恐柴禾积压空气不透熄灭,又恐挑拨太过燃烧太炽。倾听的过程,犹如观堂先生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在与故纸的牵扯易容时,时有穿越之感。看到走入历史深渊的人物在人情冷暖里像邻家老大爷的表现,时而执拗时而笑靥如花。寻觅,总归会有收获,收获来时,如暗室迎来一线光,令人怦然心动。冷坐寒窗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跟故纸打交道,在语与不语之间,只有我们对故纸的字字珍重。
就说个具体历史人物吧。
江峰青,一位19世纪末的嘉善知县,是徽州的富二代,年少得意,很年轻就进士及第。等到他分发嘉善做“七品官耳”时还年轻。他背后有实力雄厚的徽商,自带资金改造县衙环境,开设对山亭社课——一项针对嘉善学子的专项活动,旨在提高士子们科考的中考率。江峰青是科举的受益者,他自然明白科考能改变读书人的命运。当然,这也关系到他的为政声誉与社会评价,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做。年轻的江峰青也关注百姓的生计,鼓励农耕。对造成水土严重流失的制窑业忧心忡忡,提出禁开新窑,百姓不理解,而他一再坚持,因为他深知土地是世世代代百姓的命脉。晚清后太平天国时代,遭兵燹的嘉善人口骤减,加上地势低洼、丧葬陋习,县境内多暴骸,环境严重恶化,江峰青发起劝葬深埋于义冢……所有这些指向江峰青关心底层百姓的疾苦,就其行为而言,无疑是个好官。但戴丽在研究地方文献时,发现江峰青为了追求社会好誉度,也有向虚的一面。如《魏塘楹帖录存》收录其“乡人为予建长生祠属题”一联,核查文献,均无此祠的记载。仔细比对,才知道所谓的长生祠只是嘉善新安会馆某屋中为他立的一个牌位。唐吟方在整理《篆刻草》时,探知作者何尔塾之名未入史志,与江峰青有关。江曾说:“小匠恐泥,君子不为然。”清光绪版《嘉善县志》的凡例明确说“纂辑诸人,于魏塘书院拈阉派定门类,事事禀命总修”,可见这位知县在为人处世上独断专行的一面。何尔塾这位颇有成就的印学家因被视为“雕虫之技”,无缘于嘉善史志。在《篆刻草》中,何尔塾为篆刻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盖篆刻亦六艺之一,古人列于小学,虽艺成而下,亦当希冀圣贤学问之万一。其质金玉,其人帝王公将相马执事,下逮隐逸士庶,其关乎军国,岂可以为戏玩而已哉!”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何尔塾和江峰青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如此悬殊,令人唏嘘不已。但在历史的星空下,烟云散去,人们只论贡献,留下来的,都值得后人的珍视。
凝望历史烟尘,勾稽故纸,让人沉醉让人锁眉让人兴奋让人肃然起敬。如19世纪末,嘉善已经有职业摄影师进驻,并为一场文会留下合影。而此时距摄影技术传入中国没有多少年。证明嘉善人勇于接受新事物,也是素以农耕为业的嘉善在近代文明进程中有案可据的一项纪录。李正墀李达三父子为保存乡邦文献,一往情深,独任其事。在嘉善文化史上,这样可敬可佩的乡贤数不胜数。沉入故纸,才触摸到他们依然温暖的心,才懂得嘉善文化绵厚的足音里,融入了无数前辈的辛勤汗水。
就如一位老地方史研究者说的那样:从事地方文史研究的过程,是求学的过程,是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是认识历史的起点。诚望我们对故纸的“倾听”与“转述”,有助于提起人们对嘉善历史文化的兴趣,也借此致敬那些为嘉善历史文化添香积薪的先贤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