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之路
那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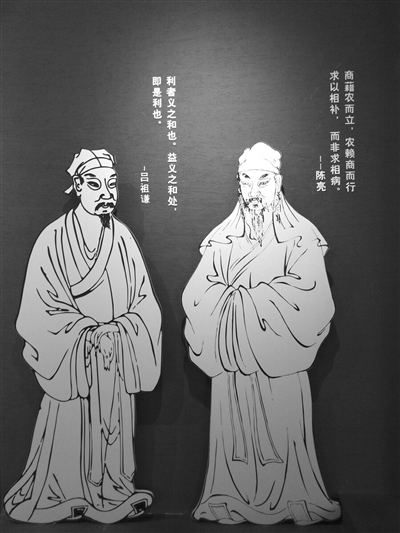 |
| 吕祖谦与陈亮画像 |
□那秋生
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前贤的论述一脉相承,提出中国近世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代。
宋鼎南移后,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孝宗乾道、淳熙之间,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都是中国学术史上坐标式的人物。吕祖谦居于浙东金华,是“浙学”的创建者;张栻初居于严州而后居于长沙,是“湖湘学”的创建者;朱熹居于闽西武夷,是“闽学”创建者,史称张、朱、吕为“东南三贤”。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后起于抚州金溪,是“心学”的创建者。总之,理学家“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浙江师范大学的黄灵庚教授经过缜密的考证与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他们频繁互访,开辟了一条南宋理学之路。这条理学之路,多是南北互动,在金华、衢州、信州、抚州、武夷之间穿梭往来,其足迹遍及现在的浙、赣、闽三省。”
起因是在《包山书院诗集》中,发现了南宋理学家的佚诗。诗集中有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张道洽、谢愕、吕祖俭以“听雨轩”为题者各一首,还有吕祖谦、朱熹以“送别”为题者各一首,共有九首。朱熹的《送别诗》:“春风江上锦帆开,送别沙头酒一杯。为客每兴先垅念,辞兄又向故乡回。松楸郁郁包山外,第宅巍巍西市隈。归至时思没祀事,清秋有约再重来。”吕祖谦的《送别诗》:“折柳长条日半斜,阳关迟唱进流霞。金乌送煖迷烟树,采鹢乘风但浪花。江水应连湖水绿,关山宜并越山嘉。鹡鸰声远同明月,先照包山孝义家。”在黄灵庚眼中,从朱熹吕祖谦的交往,串联起了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南宋理学家们的学术交流活动。他看到了这些理学家们互访的行程中,隐约闪现出的一条学术之路,于是把它称作“南宋理学之路”。
南宋倡导学术思想自由,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辨”,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他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南宋逐渐壮大的理学,成为士大夫政治的理论支撑。“道理最大”——君主头上,除了天,还多了理。从此,理学所提供的精神支撑,给后世的知识人士灌注了遗传基因,无论在政治场域,还是社会场域,不分时代,一直都显示着巨大底力。承续道统高于政统,身为臣下的士大夫可以与君主“迭为宾主”,所以有自信、有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人士在精神上便不再跪下。
南宋时期,书院大师们创立了“讲会”制度。这种学术性质的讲学活动,目的在于通过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把本学派的学旨发挥得更加深入细致;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不同的学术主张,以便兼取诸家之长相互促进。讲习式的书院,尤其是名师巨儒创设或主持的书院,往往以自由讲学为主要特色。所谓会讲,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会友讲学”。虽然在书院的学术之争中也不乏门户之见,但真正的书院大师都能做到既固守自己的宗尚,又能留意他家之长,集思广益,兼取诸家之说,充分体现自由辩论之意。
南宋思想流派纷呈,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尤其是朱子理学的诞生,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对此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