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文化理想的一个缩影
——漫评《朱明尧师友书札墨迹》
唐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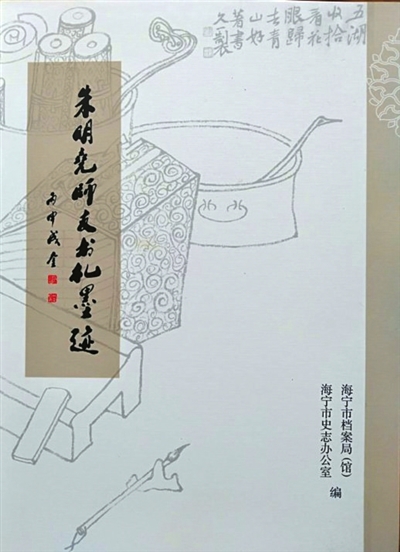 |
唐吟方
早几年,朱明尧先生就打算把自己保存了几十年的一批书信捐出去。后来他告诉我决定捐给海宁市档案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朱明尧先生是地方文史学者,长期关注海宁籍在外文化名人的行迹,追踪他们的学术动向。他在从事海宁地方史研究过程中,除了注意收集研读乡贤的撰述,与大多数传统学者一样,还与一些海宁籍名人常年保持联系,向他们请益,一边收集材料一边撰写文章,传播海宁历史文化,推介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乡贤;这中间也包括一批非海宁籍名人,因此积攒了数量不菲的书信。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书信不单是一个地方文史学者交往写作经历的见证,也是透视一个时代海宁籍文化人与海宁文化的重要文本。
关于这本尺牍书,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感触。吴世昌是当代学界著名的红学家、古典文学家,他是海宁人,自他离开故乡后,很少和海宁有联系。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朱先生主动联络吴先生,请他用毛笔书录与故乡风物有关的二首词(墨迹今已捐赠海宁市博物馆),原意是为推广历史悠久的海宁灯彩,客观上却成了吴先生留给故乡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件墨迹,弥足珍贵,此后一年吴先生即归道山。朱先生谦称自己“并非是一名书札的热心收藏者和书札文化的研究者,而是一个书札频繁往返的亲历者、耕耘者,并且又是一名受书札文化滋养的人”。他在居间扮演了“好事者”的角色,促成了故乡与故乡名人的某种翰墨因缘,晚年又举以捐赠公家,成了名符其实的乡邦文化的接力人、守护者。
另一个例子是朱明尧与左书大家费新我的通信。费老是书法名家,今天我们只知道他五六七岁时病废而改成左手挥毫,因左笔驰誉艺坛。这封信里,费老谈到他的书法创作,对出现在不同场合的作品,在内容上有自己的要求,包括钤盖印章,体现了一个指向明确的艺术立场,书写内容与形式相关联,强调书法艺术的社会功能。费老的创作还有一个特点,一些重要作品的创作,他是拟小稿的。或许与他画家出身有关,移用了绘画创作的一些的手法,显示了他严谨的艺术态度,这也是他作为书法家与传统书家的不同点,不烦推求、讲究经营。这通书信透露的费新我创作的一些细枝末节,是我们探讨当代老一辈名家创作可以征信的原始文献。
至于1973年俞平伯写给朱明尧的信里说“我过去研究《红楼梦》,其观点方法等颇多错误”。可见在“文革”背景下这位红学家的小心谨慎,未便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而海宁籍画家杨石朗的书信,厘清了一些外界误传的问题,如贺天健家藏都是印刷品。按杨的回忆“贺师处数百幅,十之七八是印本,十之二三是真迹,比吴师处临真迹多十倍”。当初王季迁、徐邦达劝说杨石朗脱离贺天健转师吴湖帆,其中一条理由是:吴湖帆藏真迹多,画画要多看真迹。而转师后杨石朗遭遇的情况并非如此,有可能涉及海上画坛名家之间的门派之争,杨石朗的书信承载着不少值得深入挖掘的信息。凡此种种,都是难得的史料。
文化人之书札信函,多文化信息,富文化内涵;往往叙文坛艺苑之事,述文朋诗友之情,兴之所至,还会将本人所作诗词楹联随抄给受件人,以交流诗心文意。我多读多研名人书简,并且也编过几本尺牍集子,写过若干关于书信文化研讨的文字,所以对此种状况深有感受。于《朱明尧师友书札墨迹》(海宁市档案局、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印,内收书札影印墨迹百余通及释文、书札作者简介),见到的前辈乡贤徐邦达、吴文祺和顾易生等的七八封信札中,多随抄着诗词联语,而我后来也知道,作为受函人的朱先生,悉数将这些作品或编入有关出版诗集,或抄录后推荐给相关文化和园林部门,委人书录后作为镌刻成的匾额和楹联,陈列于当地的东山智标塔、西山紫微阁和盐官海神庙大殿等经典建筑物上,让游人观赏。感到这样一两次的循环,就使得作为纸质的私信演变成了姓公的文化作品,其意义也就突破时空地得以放大。
朱明尧被“海上寓公”文化老人周退密称为“当代的杨敬之”,缘于他对于文化传统的信念与执着,他对于文化精英的发掘与推介,显示他作为地方文化史学者的责任感。这本《朱明尧师友书札墨迹》是他践行的文化理想的一个缩影。
面对这批内涵丰富的书札,我曾发过感慨:“名人书信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朱先生收存的这批书信,无论内容还是人选,均属难得。据我的接触和了解,在海宁,今后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群体性水平的文化资源,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会愈显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