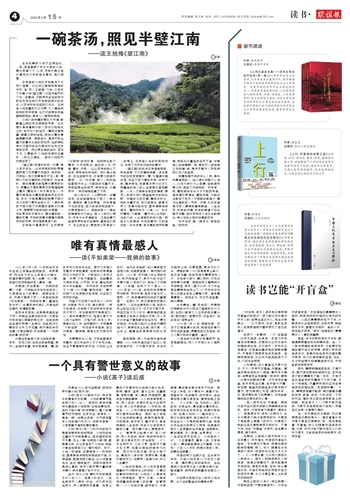唯有真情最感人
——读《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陈慈林
陈慈林
2020年4月4日,98岁的饶平如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消息甫传,网络社交平台上读者纷纷悼念。时值疫情防控期,老人后事一切从简,读者们无缘亲临送老人最后一程。
我是读《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才第一次知晓饶平如先生和夫人毛美棠姓名及故事的。追思饶老之日,我再次捧起了老人9年前出版的《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重温饶老与夫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情感故事。
在老伴去世后,他常常徘徊在留下两人共同生活痕迹的场所,沉浸在对老伴难以排解的思念中。他渐渐明白生离死别是人生常态,如能把对亡妻的怀念形之于笔墨,就仿佛老伴还活着,这是他撰写《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的初衷。
这是饶老鲐背之年才出版的第一本书。动笔之际,饶老已年逾耄耋,虽然人生阅历丰富,写书却是第一遭,因此并无文学创作经验。苦于文字难以完整抒发满腔情感,他就尝试用漫画弥补文字的不足。之前他也从未学过画,“米寿”之年方握画笔。他临摹丰子恺的风格,以苏轼、杨绛、章诒和的句子点缀画面,一页页创作,先后积累了18册、200多幅“看图说话”, 最终成就了这本装帧风格独特、内容图文并茂的作品。
作品不仅记录了饶平如个人成长史、与美棠“执子之手、偕子同老”一甲子的姻缘,还承载了中华民族近百年风云变幻。平如美棠两家虽是世交,二人却并非青梅竹马,婚姻系奉双方父母之命而成。订婚之时,平如26岁,美棠也已23岁,在民国时代,亦可算是“大龄姑娘”。平如在书中坦承,自己对美棠一眼惊艳,美棠也欣然接纳平如。
夫妻携手近60年,不可能都是岁月静好,记忆中当然少不了岁月沧桑: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平如,为抗战上过战场。当内战将临时,他以请假回家结婚为由,逃离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战场。1949年,本该随众去台湾的平如,毅然选择留下,虽然为此付出了夫妻分离22年的代价,却始终了无悔意。22年里,他吃了不少苦头:从1958年至1979年,他因历史问题被劳动教养、劳动改造,每年只能与家人团聚一次,饱尝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他却认为,其实美棠吃的苦比他更多:一名娇生惯养的小姐,在巨大政治和经济压力下,对丈夫不离不弃,独自拉扯大几个孩子,最困难时甚至到建筑工地背水泥贴补家用,还从孩子口中省下糖块寄半袋给平如。妻子去世后,平如每次路过上海自然博物馆大门,常常驻足台阶前,因为某一级台阶上,铺着当年美棠背过的水泥……
异地相思,两人只能用书信传递情感,1000多封书信见证了他们22年的艰难岁月。终于苦尽甘来,平如平反回到上海,夫妻团圆,享受天伦之乐。遗憾的是,1990年美棠患上肾炎,且逐渐加重,到后来每天需要透析4次。平如亲力亲为,精心照料,仍无法逆转妻子病情。美棠后来又罹患阿尔茨海默症,连家人都不认识,为了安全甚至需要绑在床上了,80多岁的平如像小孩般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唯有真情最感人,读到此处,我亦热泪盈眶、喉头哽咽。
此书最后一幅“老伴图”:两棵相依相偎的参天大树占了画面的五分之四,饶老以嵌有二人名字的四句藏头诗“美好回忆,棠棣开花;平生鸿爪,如此年华”结束全书。
2008年3月19日,美棠去世。平如不忍美棠凄冷孤独,就把她的骨灰安放在卧室里,遗嘱待自己去世后,将二人骨灰掺杂放置同一盒内。
12年后的农历庚子年清明节,饶老驾鹤西归,两人终于可以永久相聚了。